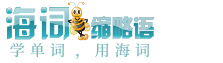英文简称 : UTP
中文全称 : 乌托邦
所属分类 : 常用词汇
词条简介 : 乌托邦 wu tuo bang 1.Utopia 2.an ideal place or state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在他写的《乌托邦》一书中,描绘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那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劳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那里没有酒店、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乌托邦 wu tuo bang 1.Utopia 2.an ideal place or state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在他写的《乌托邦》一书中,描绘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那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劳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那里没有酒店、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乌托邦用于比喻无法实现的理想或空想的美好社会。(图为摩尔《乌托邦》一书中的乌托邦地图)
什么是乌托邦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摩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乌托邦的探寻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著他的时光旅行家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鸟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或许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情境所固有的,也许它只内在于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文化之中;但是我们大可同意王尔德(Oscar Wilde)的话: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人类社会“非常乌托邦”三部曲(我不说“反乌托邦”这个名词,因为书中的不少“非常乌托邦”已经成为了现实,只能承认,反却不能,或者说很难,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包括《美丽的新世界》、《我们》、《一九八四》三部优秀小说。最早发表的是《我们》,在1920年;《美丽的新世界》发表于1932年;1948年,英国作家奥威尔以未来的1984年为名发表了《一九八四》,但前者的影响明显没有后两个。
这是三部伟大的富有激情的预言小说,政治小说,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伟大的“‘非常乌托邦’三部曲”。对于它们的作者来说,无论是赫胥黎、扎米亚京,还是奥威尔,都把丧失个性视为人类未来的最大悲剧,这种丧失或是由于科学进步或是因为来自权力的暴力。
说起乌托邦,一种解释就是尽善尽美的理想世界,或完美的最终解决。理想与乌托邦有一根本不同点,这就是理想未必是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肯定无法实现。乌托邦永远只能存在于人类的意识和文字中。乌托邦必然要有完美的性质,理想却不必。现代化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和民族的理想,但它并不等于人间天堂。追求这一理想的人也不一定将它视为问题的最终解决。理想不一定是现实的批判与否定,乌托邦却总是作为现实的对立面出现。由此可见,理想与乌托邦之间有重要的区别。但它们有一共同的本原,这就是人类希望与梦想的本能。理想是它的一般表现,而乌托邦是它的最高形式。夸父追日,西西弗斯永远推石上山,则是它永恒的象征:追求完美,而不是达到完美。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著名的《乌托邦》被称为乌托邦文学的经典。
而“非常乌托邦”是什么呢?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可以从赫胥黎、扎米亚京、奥威尔的经典“非常乌托邦”作品中找到关于“非常乌托邦”的很形象很丰富的答案。
当然,著名的“非常乌托邦”作家赫胥黎和奥威尔一再否认,社会主义、甚至前苏联,是他们“非常乌托邦”的主要目标。第一,《美丽的新世界》以美国梦的实践为基础,矛头主要指向所谓的科学主义。再者,《一九八四》则以极权主义为目标。由于《一九八四》出版于冷战时期,自然被许多人看成是冷战小说。第三,对于扎米亚京的非常乌托邦小说《我们》奥威尔在评论中说:“扎米亚京似乎针对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国家,而是工业文明所含有的目标。”总之,无论是赫胥黎,奥威尔,还是扎米亚京,他们笔下的“非常乌托邦”行为,实际针对的并不是某一特定的乌托邦,而是现代乌托邦本身。
非常乌托邦三部曲
一、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 《美丽的新世界》是阿道斯.赫胥黎发表于1932年一部优秀作品,又是作者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代表作。阿道斯.赫胥黎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天演论》作者老赫胥黎的孙子。这部小说是从生物学角度把未来社会描绘成“共有、划一、安定”的孵化室,全体社会成员一律由试管统一孵化而出,千人一面、万众一心。而书中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因孵化事故制造出来的异类、那位到处碰壁的倒霉蛋。 具体地说,《美丽的新世界》预测了600年后的世界。书中描写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代替了上帝,因为福特发明了生产汽车的流水线,使生产飞速发展,这种生产方法终于统治了整个世界,公元也因此变成了“福元”。在新世界里,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安于自己的“等级”,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亨用定量配给的“索麻”——一种让人忘掉七情六欲、“有鸦片之益而无鸦片之害”的药品。作者描写了一个保留区内的“野人”,他来到了盼望已久的“新世界”,开始时为物质环境的改变而涕零,欢呼到达了——美丽新世界,随后终因他还有血性,无法适应在流水生产的社会中的白蚁式的生活,加上他认为自己的心上人放荡而无法忍受(新世界的名言: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人。故无所谓“放荡”可言),使他最后的精神寄托破灭,终于在孤独、绝望中自尽身亡。在这个“新世界”里,社会安定就是一切,影响安定的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及各种差异荡然无存。“野人”的形象就是今天人类的化身,他的处境和悲剧结局令人不寒而栗。 作为小说,《美丽新世界》的情节性并不强,“登场人物都是思想”,可见本书的写法不同于一般,作品不是以形象,而是以给人类带来思索的余地取胜。同时,“这本书和其他预言式作品不同之处乃在于它并非产自直感,而是源于冷静的知性”。通过这本小说,我们大致可领略这位二十世纪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作家的深刻思想和写作风格。 《美丽新世界》曾被评为二十世纪十大小说之一。它的特点是在叙述未来的情景时,敏锐的思路透彻地写出了知识分子在机械文明高度发达时,精神上受到压迫的痛苦、孤独无助的状态。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生物学、心理学知识,使这些描写具有撼人的力量,使读者可以从作者深刻的思想获益匪浅。
二、扎米亚京的《我们》 《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身处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他本人被称为“语言大师”、“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代宗师”,他说过:“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怀疑论者创造,而不是那些精明能干、忠诚的官员创造。”的确,说起扎米亚京,我的一位朋友说过,一度畅销流行的希区柯克的悬疑故事里,至少有两篇是直接从文学大师的作品中吸取了营养。一篇是《报复》,脱胎于英国作家毛姆的短篇小说《午餐》;一篇是《谋杀1990》,换骨于俄国作家扎米亚京的长篇小说《我们》。由此可见《我们》的深度和作者才华的惊人影响力。 《我们》是一部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长篇小说。讲述“我”——未来的大统一王国的数学家、设计师的故事。大统一王国由大恩主领导,人们高度一律,都没有独特的姓名,只有编号。我是号码503。这个王国的人们连作息都严格按照王国发下的《作息时间戒律表》来进行。王国的人们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对象,而是在统一领导下由王国的有关机构指定。给那些编号的男女发一种粉红色的小票,让他们凭票进行性生活。比如今天男号码503的性对象就是女号码O-90。但是503也偷偷地看点禁书,发现古人居然还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说还生活在无组织和野蛮之中。“使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怎么能允许人们生活中没有我们这样的守时戒律表,对用餐时间不作精确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觉。有的史学家还谈到,当时的街上好像灯火彻夜通明,车马行人通宵穿行不息。” 更令号码503奇怪的是:“这个国家居然对性生活放任不管——这真是咄咄怪事:不管是谁,在什么时候,进行多少次,在什么地点……都由着人们自己,完全不按科学规律行事,活像动物。他们也和动物一样,盲目随便地乱生娃娃,真让我觉得可笑!” 这个大恩主领导的大统一王国充满着很多科学的创造发明,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些古人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眼中,他们已经科学进化得近乎完美。比如,他们已经用科学手段来写诗歌了,把数学法则融入诗歌之中。又比如说,他们天才性地创造发明了“一致同意节”。 由于号码503受到古书的异端邪说诱惑,以及克制不住自己体内的古老欲望的复苏,503的思想被国家护卫局侦破,最后被送进了一种叫作“气钟罩”的刑具里处死……当然这个大统一王国里已经有不少号码已经背叛了理性。“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又哭又喊,又是尸体,又是野兽……” 故事似乎是在一种谢主隆恩的气氛中结束。号码503在临死前坚定了对王国理想的信念:“40号横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
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说起奥威尔,他或是政治上的悲观主义者,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作为预言,《一九八四》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作为告诫,它是值得人们深省的。这句广泛传播的“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老大哥在看着你呢!”便出自《一九八四》。书中的“我”(温斯顿)生活在大洋国,当时是一九八四年,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政府的职能部门分为真理部、和平部、友爱部和富裕部,“我”在真理部,编造着真实的谎言,“我”知道“我”迟早会被思想警察处死,可是“我”还是在找寻生活的本来面目和被湮没的难以找寻的可能的真相: 有一天,一个女人跟我说“我爱你”,我们开始了胆战心惊的爱情,因为党员是不需要感情的,只有那些粗俗的无产阶级才具有的东西。我还梦见一个人在黑暗的走廊跟我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这是一个意外而又意料中的结局,我终于遭受了一切可能的毒打和刑具,我招供了一切可能的人的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罪行,我将我的爱人(朱丽叶)的我所知道和不知道的一切我都说了,可是我还是说,“我没有背叛她!”的确,我还爱她。以后的日子,我终于由于在感情上的不悔过进入了101房间,这里有什么,有人不能不服从的东西,而我最怕的是老鼠,他拿来了一个面具,里面有两只老鼠,都已经成年,其中一 只已经老了,毛稀落,大多褪去,它勉强地爬到边缘等待着美食,我可以想象一会他们在咀嚼我的肉,啃我的骨头,终于我想起有一个人可以救我,“咬朱丽叶!咬朱丽叶!别咬我!你们怎么咬她都可以。把她的脸咬下来,啃她的骨头。别咬我!朱丽叶!别咬我!”然后我向后倒去,掉进了深渊,离开了老鼠,彻底坠落。我失去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点温暖的东西…… 这就是《一九八四》,最后那一段的惊心动魄让读者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恶心,无限的悲哀……虽然《一九八四》的问世,一种说法是奥威尔有感于纳粹暴政和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极权而作,但谁也不怀疑它言中了西方“自由世界”的许多方面,而经历过众多非常时期的中国读者又怎能对温斯顿的遭遇无动于衷? 目前,国内尚无一本全部收集“非常乌托邦三部曲”的文集(三部小说不超过50万字),但是分开出版的已经有很多,如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翻译的《一九八四》,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前《苏联文学》主编顾亚鸣女士翻译的《我们》(作家出版社),著名翻译家孙法理翻译的《美妙的新世界》(译林出版社出版),以及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精华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散文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对照的《一九八四》、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远方出版社出版的《美丽新世界》等。今后,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希望能有一流的出版社尽快策划类似选题,鼎立出版三册合一的非常乌托邦文集,以满足读者、收藏者和市场需要。
- UTP : Unshielded Twisted Pair (Cat 5 network cabling) Unshielded双绞线(猫5网络布线)
- UTP : Unshielded Twisted Pair 电话用无遮蔽双绞线
- UTP : uridine triphosphate 三磷酸尿苷
- UTP :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城市道路规划设计
- UTP : Under The Pump (military slang; chiefly Australian) 在泵(澳大利亚)的主要军事俚语
- UTP : Universal Time Protocol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协议
- UTP : Uncertain Tax Position 不确定的出口退(免)税的位置